 58.番外一(中) 烈途
58.番外一(中) 烈途
 58.番外一(中) 烈途
58.番外一(中) 烈途
反,连带着伤到的左胸也隐隐作痛,她在床上翻来覆去,想要重新入睡却很困难,翻出手机看时间,才夜里十一点。徐途在黑暗中睁着眼,一想每天这时候正蹦迪打牌飙车呢,也难怪会睡不着。
又挺了片刻,徐途翻身下床,开了灯,慢步踱出房门。
院子灯还亮着,她四下打量一遍,隐约看清整座屋舍构造。院子很大,当中摆着长桌和板凳,角落里有一口压水井,旁边水泥高台搁着几簸箕晒干的萝卜和山蘑,徐途弓身凑到鼻端闻了闻,嫌弃的直皱鼻,继续找厨房。这个院子其实很简单,对面是大门,其余三面都是房间,独门独窗,几乎每扇门都关着。
徐途挨个儿推了推,终于,西面矮房的门开一道缝隙,找不到开关,她摸黑进去,淡薄的月光从窄小窗户照进来,眼睛渐渐适应黑暗,徐途知道这间就是厨房。厨房设备简陋,却胜在井井有条,锅碗瓢盆规矩摆放,灶台干净整洁,角落竹筐堆放今天采购的土豆和绿叶菜,全部是生食,冷锅冷灶,半个馒头都没找到。
徐途按着肚子出来,想回去嚼个泡面充充饥,走到拐角处停了停,原来,那两排房子之间并非相连,当中留有两人宽的空隙,有稀疏光亮从后头透过来,伴随孱弱的水声。
她脚尖转了个方向,没等过去,却见一人擦着头发走出来。
徐途一惊,不由自主从上到下扫了眼。
秦烈只穿一条垂感强烈的黑色宽腿裤,裤腰卡的位置偏低,两道胯骨凹凸有力。他上身,月光中,肌肤还朦一层水汽,宽厚的肩膀下,胸膛、手臂线条流畅,腰很窄,中间嵌着深深的肚脐。他单臂举在头顶,还维持擦头发的动作,显然也看见了她,脚步滞住。
两人对视几秒,“有事?”秦烈放下手臂,抖开另一手抓的背心,迅速套回身上。
眨个眼的功夫,一片布料霎时遮住他身前的风景,只露两只强健手臂。
徐途脸有些热,别开眼,安慰自己“白看的,谁不看”。
&事。”她答。
秦烈直接走开。
徐途回头:“等等,”她眼神跟过去:“有点儿事。”
他停下,把毛巾搭在肩膀上,微侧着身看过来,等她说话。
徐途问:“还有吃的吗?我饿了。”
秦烈往远处看了眼,想想答:“这个时辰了,应该没有。”
他说话永远都是一个口气,冷静淡漠,不带任何情绪,徐途听了没来由火大,从前在一群玩伴里,出身和家庭的缘故,她都是中心,被别人众星捧月,十分接受不了这种冷淡态度。
徐途冷哼一声:“这就是你们的待客之道?我大老远跑过来,在攀禹县吹一晚上西北风不说,还碰到个疯子。现在饿了,一口饭都吃不上么?”
&是客?”
徐途一噎。
秦烈说:“这不是酒店或者度假村,随便你什么时候叫餐都有,吃饭时间干什么去了?”
徐途立即答:“吃饭你没叫我。”
秦烈停滞片刻,稍微回忆,想起晚上他和阿夫吃的牛肉面,叫过徐途,但她没过来。
他重申一遍:“以后饭点儿吃饭,过期不候,别指望别人上赶着去请你。”说完往后指了指:“那里头能洗澡,注意节约用水。明早开饭时间是六点。”
&有,”秦烈走两步,回过头又说:“刘春山是疯子,今天事出意外,你跟他一般见识也没意思,往后见着躲着点儿。”
徐途无言以对,先前还信誓旦旦,准备对他打击报复,现在他一番话竟全是道理,一时语塞,根本找不到理由还击,好像她一晚上受的委屈都是小题大做。
徐途气不过,往前紧跑了几步,想要狠狠推开他冲到前面去,他身后却像张了眼睛,稍微侧身,一只大手便将她两个手腕同时擒住,用力提起。徐途双臂被迫高举,脚后跟离了地,整个身体不由自主贴近他,他身上还有残余的皂荚香。
徐途咬咬下唇:“你放开。”
 妙手小村医 简介:“要想治病,先看颜值!”乡村小医生林昊向来坚持原则。原本只是个默默无闻的打工仔,谁知医术却高得无边无际!林昊一出手,疑难杂症都没有,不仅治好了大人物的男人病;更在治好了大美女的女人病!从
妙手小村医 简介:“要想治病,先看颜值!”乡村小医生林昊向来坚持原则。原本只是个默默无闻的打工仔,谁知医术却高得无边无际!林昊一出手,疑难杂症都没有,不仅治好了大人物的男人病;更在治好了大美女的女人病!从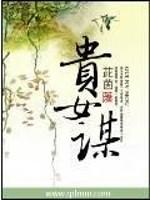 贵女谋 宅斗是可怕的苏九一向知道,真正穿越了这才知道宅斗要素中的猪队友狼对手都可以弱爆了,可怕的是披着羊皮的狼队友,叼着血淋淋的肥肉硬要她吃下,再肥美的肉也是人肉啊!这怎么破?
贵女谋 宅斗是可怕的苏九一向知道,真正穿越了这才知道宅斗要素中的猪队友狼对手都可以弱爆了,可怕的是披着羊皮的狼队友,叼着血淋淋的肥肉硬要她吃下,再肥美的肉也是人肉啊!这怎么破?
 我的女神是只猫 遇到一只小女孩,她说自己叫“南猫猫猫猫猫”,是一只猫,正在寻找自己的大将军,征服地球,奴役全人类!
我的女神是只猫 遇到一只小女孩,她说自己叫“南猫猫猫猫猫”,是一只猫,正在寻找自己的大将军,征服地球,奴役全人类!